文/張竣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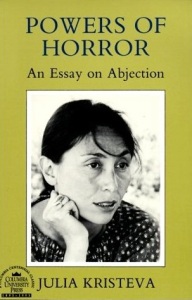
「噁心」是主體的心理感受。主體在看見某些骯髒的人事物時覺得「這東西很噁心」、「這人很噁心」,甚至撞見某些行為時也是如此。但「噁心」同時涉及物質基礎與社會結構。那麼,「噁心」究竟源於什麼樣的心理動力和社會文化?
克莉斯蒂娃(Julia Kristeva)的理論推演有點龐大,遠非一篇引介可以完整陳述。不過要了解她在《恐怖的力量》(Powers of Horror)中如何處理這個問題,必須先了解幾個關鍵概念。人類所使用的語言,其實在溝通過程中承載、潛藏、衍生出種種社會規範。這些規範雖然是人類透過語言建立的,但規範也透過語言的傳遞,反向形塑人類的認知,甚至成為壓制人類的力量。我們可以把「語言」的概念擴大,從明確說出來的話、能做的事,衍生至種種「沒說出來的潛規則」,包括意識形態。人所仰仗的語言、規範、分類方式與意識形態彼此交織,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秩序,也就是語言結構中的「象徵界」(the symbolic)。人類依賴這個社會中的語言結構生存,每個人也成為承載社會意義和語言結構的「說話主體」(speaking subject)。
但是人作為說話主體,並不只是單純地受制於語言結構。人類在溝通、行動的過程中,可能會出現越出常規的情形。「當我尋找〈自己〉、失落〈自己〉,或享受歡愉時,『我』便擁有了異質性」(13),也正如劉紀蕙教授在該書導讀中所說的:「『說話主體』是分裂的主體,擺盪於社會結構制約與無意識欲力的兩軸之間」(xx)。換句話說,人明明身為說話主體,卻可能因為無意識欲力的驅動,越出常規,引發整個語言結構、乃至社會結構的崩壞。經典電影《大法師》(The Exorcist)中的小女孩麗根被惡魔附身,從小女孩的單純形象漸漸崩壞魔化,甚至還能將頭部一百八十度轉向。雖然這個過程的前後差異相當巨大,但究其源頭也是以一個普通人類的身體漸漸形成的恐怖軀體。說話主體所承襲的語言,在人們重複訴說運用的同時也不斷地旁逸斜出,演繹成「惑眾的妖言」。電影後段神父需要以除魔儀式,驅逐麗根體內的惡魔,則是試圖恢復結構秩序,再度鞏固象徵界的劃定。
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無意識欲力,在背後驅動這股滲透象徵界、使之崩壞的力量?克莉斯蒂娃檢視了佛洛伊德在《性學三論》(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)中的自體性慾期說法(auto-eroticism),並將眼光轉向《圖騰與禁忌》(Totem and Taboo)一書中對於自戀的解釋。佛洛伊德認為,孩童在自體性慾期之後,以及意識到父親權威的伊底帕斯期之前,其實有一個中介階段。不同於伊底帕斯期中孩童已經認知到主客二分的情況,在這個中介階段中,主客關係還沒有完全建立,力比多(libido,或譯原欲)朝向的是一種「非客體」(non-object)的事物。
換句話說,這個性驅力雖然朝向看似「客體」的事物,實際上它仍然沒有與自我完全分裂,成為完全的客體。克莉斯蒂娃認為,孩童的這段經歷讓他在日後即便進入伊底帕斯期,仍會不斷受到這個中介階段影響。主客無法截然二分的結果是主體無法確立身分認同。在這個「前伊底帕斯」(pre-Oedipal)、沒有父親意識的階段中,主體的認知是母子一體的連帶關係,因而性驅力其實也是朝向母體的。缺乏外在客體意識的自戀階段也正是克莉斯蒂娃所說的「符號界」(the semiotic)的來由。符號界不分主客的語言特性威脅到主客分明的象徵界,導致父系秩序的崩壞。也因此,在主體秩序進入伊底帕斯期,進入語言結構以後,父系象徵秩序會對主體設下重重禁忌,壓制自戀階段形成的符號界。
禁忌、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連結,是賤斥理論的重要貢獻。前面所說的語言結構論,雖然可以解釋不同主體之間的溝通方式,卻無法解釋為什麼主體會有失控的可能。而克莉斯蒂娃則將眼光轉向了語言結構所設下的邊界(意即禁忌),開啟了陰性(the feminine)如何對結構造成威脅的理解進路。
以父系為代表的象徵秩序為了防止主體的自我認同崩壞,將出自於「陰性空間」(chora)、尚未受到象徵秩序制約的相關事物排除,此即「賤斥」作用(abjection)。這個過程是克莉斯蒂娃在個體的層次上推演出來的。她從嬰兒對於乳狀食物的作嘔,認為這可能是賤斥最原初的表現形式。父母所餵食的食品對嬰兒來說雖然是必須的養分,但父母同時代表被象徵秩序所設定的「我」的觀念,因而餵食其實也是將嬰兒納入象徵秩序的過程。嬰兒在「賤斥」食物的同時,冒著吐盡養分的風險,展現自身與象徵秩序之間難以結合。我們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,主體其實也在展現自己成為整個象徵秩序之「賤斥體」的可能,具有模稜兩可、相互矛盾的特性。
賤斥最具代表性的例子,其實是被認為污染性質強的糞便和經血。排出糞便和經血是人體為了維持生命的必要過程,因此糞便與經血可以引申為主體在形成自我認同的過程中,勢必要排出的賤斥體。不過克莉斯蒂娃也從人類學和文學中的諸多案例,將這兩個例子用作區分內在和外在兩種力道方式。糞便、尿液、屍體是令生者感到死亡威脅的事物,而經血則是從身份認同或社會內部產生的、威脅著某種既定秩序(例如性別)的物質。這些物質都具有很強的「邊界性格」,座落於生/死、男/女、乾淨/汙穢、神聖/褻瀆等等界線之間,雖然被主體和結構排除在外,然而主體和結構卻要靠著這些賤斥體的存在和界線劃分,才得以反過來定義自身。
對於克莉斯蒂娃來說,符號界往往要等到象徵界的某些禁忌遭到觸犯時,才稍微容易被人察覺到其毀壞結構的潛質。禁忌不論涉及到糞便、經血、亂倫或褻瀆,都逾越了父系語言結構,重新喚醒主體對於陰性空間的記憶,回到「人尚未成人」,一切尚未被清楚劃界的太初混沌中。
引用文獻
Sigmund Freud.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. New York: Basic, 2000.
______. Totem and Taboo. New York: Norton, 1990.
克莉斯蒂娃著,彭仁郁譯。《恐怖的力量》。台北:桂冠,2003年。